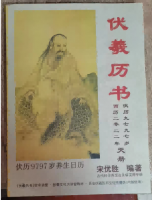行业头条
个人养老金市场助力 保险资管迎发展新机遇
近年来保险资管公司资产管理规模数据来源: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 2018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发布,作为资产管...[详细]
前10月装备制造业利润明显回升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10月,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3.2%,增速较1至9月加快2.6个百分点,连续6个月回升;10月当月,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25.9%,实...[详细]
我国首座深水科考专用码头启用
新入列的“海洋地质二号”多功能新型科考船18日缓缓抵靠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科考码头,标志着我国首座深水科考码头正式启用,我国深海探测基地保障...[详细]
中国贸促会:多措并举助中国企业出海拓商机
记者15日从中国贸促会了解到,应出国展览行业和外贸企业需求,中国贸促会及时推出恢复出国经贸展览的针对性举措,已完成今年11月至明年2月期间的15个出国经贸展...[详细]
专家论坛
白明:中老铁路开通一年,折射出怎样的合作前景?
中老铁路,又称中老昆万铁路,它北起云南省昆明市,南至老挝首都万象市,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首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全线采用中国标准、使用中国设...[详细]
金观平:切实稳定市场主体政策预期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切实稳定市场主体政策预期。今年以来,党中央...[详细]
何建华:推动共同富裕,重在实践中听微决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全民共识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深入人心...[详细]
杨忠阳:从更深层次看汽车消费
汽车销量预期从悲观转为乐观,一方面在于新冠肺炎疫情得到较好控制,另一方面则在于国家对汽车消费的重视。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标志性产品...[详细]
行业人物
袁运生

袁运生,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生于江苏南通。一九六二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一九七九年参加首都机场壁画创作,先后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任教。一九八二年应邀访美并任教于哈佛大学等几所大学。一九八八年起在纽约当职业艺术家。一九九六年九月返国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四画室主任、教授。曾在国外举办二十多次个人画展。
主要作品
主要作品有: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一九七九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图书馆壁画《红+蓝+黄=白?——关于中国两个神话故事》(一九八三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型丝织壁挂《人类寓言》(一九九六年),油画《水乡的记忆》、《眼睛》、《追— —末班车》等。有作品被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出版有《云南白描写生集》、《运生素描》、《袁运生素描集》、《袁运生画集》。
人生经历
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
1978在云南博物馆举办个展。出版“云南白描写生集”。
1978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同时创作北京国际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1980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任教。
1982年应美国政府邀请访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安排访问德·库宁、劳申伯、乔治·西戈等艺术家并在纽约举办演讲会。
1983年应聘为波士顿塔夫茨大学访问艺术家。应邀为该校图书馆创作壁画《红+兰+黄=白(关于两个中国神话)》。
1984年应聘为哈佛大学访问艺术家,同时举办讲座和个展。
1985年继续应聘至1987年为哈佛访问艺术家,教授素描并多次举办讲座。参加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壁画会议。
1987年在纽约苏荷区画廊举办个展。
1988年应邀参加汉城国际奥林匹克艺术大展,作品为韩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
1988—1996年在洛杉矶、纽约、伦敦、阿姆斯特丹、台北、北京国际艺苑、剑桥等多处画廊举办个展。
1996年应邀参加其创作巨型壁挂“人类寓言”在哈佛大学揭幕仪式。应中央美术学院靳尚谊院长邀请回国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四画室主任至今。
1997—2001年多次应邀参加国内重要提名展,二十世纪大展,油画百年展及多项学术研讨会。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常委。
1979年10月,由张仃、袁运生、袁运甫等艺术家共同创作的首都机场壁画宣告完成。

袁运生正在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创作巨幅油画作品
刚刚通航不久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以其独有的建筑风格和艺术氛围成为全球关注焦点。此时,一位参与新机场艺术品创作的老艺术家尤其受到公众关注。他就是曾在1979年为首都国际机场创作了壁画《生命的赞歌——泼水节》的袁运生。1979年10月《北京日报》接连刊登了《崭新的航空港》《喜看壁画的复兴》两篇文章,介绍这幅壁画作品并探讨壁画艺术的复兴。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在不同年代、不同事件中,坚持自己艺术追求的道路始终不平坦,但袁运生选择坚持自己的初心。
毕业创作引两位老师争执
1955年,袁运生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美院。走进这座艺术殿堂后,他发现自己首先面临艺术道路的选择。在彼时历史环境下,艺术造型观念一边倒,学习苏联。袁运生受老师董希文先生的影响,在学术观念上选择将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造型语言相结合。这个主张影响了袁运生一辈子。
还在央美读书期间,袁运生就成了“右派”,被遣往北京东郊的双桥农场改造。可天性乐观的他却将这段经历当作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他不仅在劳动中强健了体魄,还利用放羊、养猪等机会,画了十几本动物速写。更难得的是,在农场,他与江丰、李宗津、冯法祀等多位在艺术上有明确主张的先生们同住一间宿舍,在和先生们的思想交流中,他更坚定了自己的艺术主张。
两年后,袁运生回到学校继续学习。1962年毕业前夕,袁运生在江南写生两个多月,重振作画的信心,并在这次写生基础上创作了本科毕业作品——油画《水乡的记忆》。画面以苏州郊区的甪直镇为灵感,将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现代主义造型语言相结合,绘出了他对江南古镇的感觉。“有大量写生垫底,创作画面中的人物时不需要模特儿,甚至创作时连写生也丢到一边去,结果画出来却比写生更接近我的感受。可能,这就是真诚的力量。”老师董希文非常满意这幅作品,给出了满分5分,而主张全面学习苏联造型语言的李天祥给出了2分,两位老师争执不下,最终给了4+。“不久,批评这件毕业作品的文章登在杂志上,说这张画里的人被丑化了,我不禁哑然。也许,我丢掉真诚,就会取得赞美。”袁运生不愿背离自己的艺术主张,只是他没想到,为了这份坚持,他在之后的十几年里竟一事无成。
毕业之际,即便美术大家庞薰琴先生亲自来到央美要人,希望他可以去中央工艺美院从教,但最终他还是被分配到吉林省长春市工人文化宫,成为一名专门辅导业余绘画爱好者的老师。在长春,他一待就是18年。直到1978年,他接到了一个热情的邀约。
央美的老同学,当时已在云南站稳脚跟的丁绍光、刘绍惠、姚钟华、孙景波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前去西双版纳和临沧傣族地区生活、创作几个月。自由创作,这是一个久违的词,是他内心的渴望。他鼓起勇气向单位请假,一向惜才的长春市总工会主席贺英亲自批准,老同学费正借了三百元钱给他,终于促成了这次采风创作。
8月,数十个小时的周转颠簸后抵达昆明的袁运生,把前来接站的四个同学吓了一大跳。为了这次采风,他定做了大大小小一百多个油画框,把四个同学的空自行车全都装满了。同学们打趣儿,“你这是打了家具来卖啊。”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一次采风将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赴美14年更坚定艺术道路
首都国际机场壁画改变了袁运生的命运。1980年6月,在东北待了18年后,青春已不再的袁运生被调回中央美院任教。1982年,他应美国国际交流总署邀请,赴美做访问学者,后来又留在纽约成为自由创作的艺术家。这一去,就是14年。
许多人以为他不会回来了,可袁运生在美国却以另一种方式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艺术道路该有的方向。
“刚去访问的时候,我被安排见了美国许多优秀的艺术家,包括抽象表现主义的灵魂人物之一威廉·德·库宁。”袁运生拿了自己在云南采风时的部分白描作品给德·库宁看,引起了这位荷兰裔美国画家的强烈创作欲望。“我想立刻画画了。”德·库宁当着袁运生的面开始了创作,创作结束画面还未干,他就把作画时使用的一支最大号油画笔送给了袁运生。“从这一次交流可以感受到,艺术可以跨越语言障碍,获得共鸣。而中国传统的白描艺术,也完全被现代艺术家所理解和接受。”在美国绘画交流的那些年,袁运生毫无疑问拓宽了自己的艺术创作思路,也学习了西方当代艺术的种种特色。“在美国期间创作的一些作品,有抽象的、有表现意味的,但这些探索并没有延续下去。”他在美国期间为塔夫茨大学创作的壁画就以中国传统神话《女娲补天》为题材,另一幅在美国创作的丝织壁挂《无题》也是在中国传统艺术思路指导下进行的创作。
“美国艺术界常常隔一阵子就一种主义压倒另一种主义,把‘变’看成最根本因素。美国艺术界还宣布绘画和雕塑已经死亡。我不认同。”袁运生觉得,这样的结论很可笑,他觉得是时候回到祖国了。这时,母校中央美术学院也向他发出了回校任教的邀请。
1996年,袁运生回到中央美院油画系,在第四油画室任教。时任央美校长的靳尚谊原本认为,袁运生对西方当代艺术非常了解,可以加强第四油画室现当代艺术方面的教学,并且专门安排了一次演讲,请他讲讲西方当代艺术。演讲那天,礼堂里坐满了人,大家等待着他对美国当代艺术各流派点评分析的激昂陈词,没想到,却迎来了一次主题为“我们必须走中国自己的路”的宣言。他呼吁,中国美术教育应该建立自己的教育体系。

走遍200多个县
寻找艺术本源
“回国后,我清晰地认识到,在艺术教育上走中国自己的路,将是我余生的唯一追求。”袁运生说。说到做到,他一开始上课就带着学生下乡考察、看石窟。“为什么看这些?造型艺术从素描开始,而高等美术教育中的素描对象全都是西方雕塑。若想建立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首先得有本土研究素材做支撑。我国历史留存下来的众多雕塑朝代不同、材料不同、造型不同、风格不同,这些却从来没有纳入到教学中。”袁运生身体力行,组织了一支研究团队,要为重建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体系做准备。
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袁运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做古代雕塑的普查和遴选工作。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10年时间,他带队跑了陕西、山西、甘肃等19个省200多个市县的博物馆、石窟、文化遗址和寺庙。资金有限,他带领团队背着大包小包,火车倒长途汽车,长途汽车倒三轮车,奔走在山岭之间。更难的是,许多单位即便见到了国家文物局的信函,也不愿意让他们进去为文物雕像临摹。“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不客气,站在门口就吵起来。”袁运生笑着说,别看自己身材瘦小,但是脾气耿直,吵起来很有些气势,不达目的不罢休,不少单位怕了这老头儿,只好让他进去画画。
经过一段时间积累后,2002年,他提出“复制中国古代雕刻进入基础教学”的思路。2005年,他又进一步提出课题“中国传统雕塑的复制与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并在同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届文化部创新奖”,这项课题也因此成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2010年,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批示财政部、文化部、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对后续研究工作给予支持。国家一系列的支持,让袁运生更有了底气。
“不光临摹,还必须把这些雕像复制下来。”袁运生说,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泥塑和带有彩绘的雕像无法翻模复制,可以复制的雕像类别本就受到限制,而且还要挑选造型水平高的造像。经过10年积累,如今他率领的团队已经以石膏原比例复制了山西南涅水石刻博物馆的29种佛造像、山东诸城博物馆的36种佛造像,复刻作品年代涉及北魏、东魏、北齐。他们还以青铜原比例复制了首都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山西永济蒲津渡遗址博物馆总计71件青铜器。被复制的青铜器,包括著名的商代青铜器后母戊鼎和唐代的两组黄河大牛。
2017年11月《北京日报》刊登一则题为《央美成立中国传统造型研究中心》的消息。这篇报道透露,袁运生被聘为该中心主任,将围绕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脉络与传承展开研究。
今年,袁运生已经83岁了,无法亲自带队奔波了,他关心的是,已经积累的这些素材如何进入教学体系,“这是个大工程,希望我能看到高等美术教育的教学中,真正用上它们的那一天。”